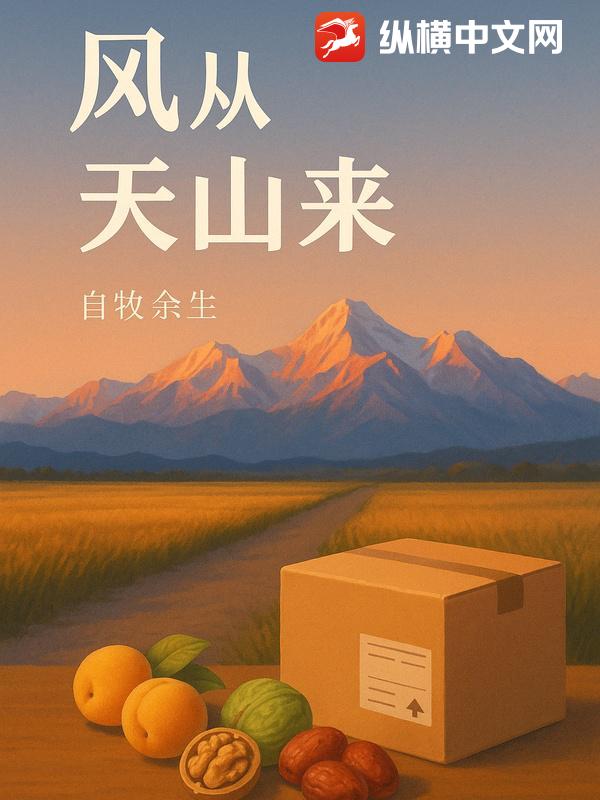玉尔达的院子傍晚又亮起那盏黄灯。灯影落在白墙上,像有人用手掌轻轻抹了一下,留下温和的痕。
县里的宿舍楼里,李明把电脑合上,又打开,指尖在键盘上停了两秒:他把“统一”和“保留”写在同一行,中间没加标点,就那么挨在一起——他要想办法,让这两件看着像要打架的事别真打起来。等他回去,再跟大家坐一桌说清楚。
手机震了一下,是“玉尔达工作群”。
苏蔓发来两条视频:院门口的公示栏换了纸,字写得干净,核桃、枣干的价目、规格、承诺一条不漏。
赵书记把落叶扫成一小堆,又用扫帚头在地上轻轻按了一按,像给它找个稳当的角。李明看着,心里那口气慢慢归回原位。
“白板又补了两条。”古丽发语音,声音带着一点风,“第一条写‘只收自家货’,第二条写‘来路要写清楚’。
今天有人拎着外村的枣说‘就贴你们名儿’,我说不行。他脸色难看,我让他坐下喝口水,再慢慢解释。他还算听得进去。”
“做得对。”李明回,“咱们不是不帮忙,是规矩先在那儿。谁都一个样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古丽笑了一声,“你讲的那四句我记得。”她指的是李明在县里板书时写的那几行:怎么收、怎么装、怎么说、怎么赔。
李明靠在椅背上,仰了仰头。窗外有火车过,声音压得很低,像从天山那边刮来的一阵夜风,穿过县城和玉尔达,往更远的地方走。
他忽然想到那句玩笑:“车稳,人就稳。”买买提江常这么说。他笑了一下,给古丽回了个“稳”字。
院子里,苏蔓拎着手机在走廊里来回,手背贴着屏幕挡光:“今晚视频我来录,两件事,一是有人借名儿,二是我们怎么写来路。话我大概捋好了。”
古丽把桌上的样袋、贴纸摆齐,顺手把一只歪了的箱子扶正:“别太硬,像平时说话那样就行。要不然又有人说我们端着。”
“成。”苏蔓点点头,把发卡夹得更紧。她把镜头对准桌面,压低声音试拍:“大家好,今天两点说明:第一,我们只收自家乡亲的货。外村的想合作,不是没机会,但要写清楚来路,咱不能糊弄人。第二,贴名儿这事,不是谁都能贴,我们背着这个名儿,心里是有数的,所以要对得起它……”她读到这儿,自己先笑了,“行不行?”
古丽笑出声:“行,像你本人说话。”
“那我发了。”苏蔓点下“发布”,又把评论区置顶改了几句,删了一句多余的客套,留了一句最重要的话:有疑问留言,我们看见就回。
吐尔逊从街口晃进来,胳膊上搭着一只干净的布袋:“小李还在县里?我那边冷柜温度一直稳着,你让他放心。”他把手机递过来,上面一张照片——数字停在“4”。李明让他每天发一张,成了习惯。
“放心。”古丽点头,“今晚拼车那两趟,还是你这边先放,别让它多站一会儿。”
吐尔逊摆摆手:“都懂,放心。你们该做啥做啥。”
买买提江把车倒进来,车灯扫过院墙,留下一道窄窄的亮。他把窗摇下一半,探出头:“今天枣装得齐不齐?我把路线改了下,先走东线,再去西线,路上不堵。”
“齐。”古丽回,“优先走外省那批,省内的放后头。别问为什么,晚上风凉一点,路上好走。”
买买提江竖了一下大拇指,脸上那条笑纹顺着光滑了一下:“你懂这门道就行。”
县里的教室里,李明没用PPT。他把那只样箱又摆上讲台,手上动作慢而稳,像在屋里搭梯子。
他用胶带划过纸面,压紧,抬头,目光扫一圈:“你们别觉得这是小事。就这么一个压的动作,能少多少麻烦。你每做一次,心里头那道线就直一点。”
有人举手:“我们站点没你们人手那么齐,咋办?”
“少不怕。”李明把胶带放下,“活拆开,别求全,求顺。就像你们家修大门,先把门框立直了,门扇先别想那么花。你把人安排稳了,一个人盯一件,先盯住,别飘。”
“那坏了咋赔?”
“先别谈赔。”李明笑,“先谈说清楚。说清楚了还坏,再谈赔。就这么个顺序。”
后排有人低低笑了声,小声嘀咕:“说得倒像回事。”李明没接茬,把黑板上“怎么装”那一行又重重划过两道,白粉末在黑板底沿积了一小条。他转身:“你们看懂了没有?”
有人点头,有人“嗯”了一声。李明把箱子推到台阶下:“围着看看,手摸一摸。你自己摸过一次,回去就知道力道了。”
窗外风灌了进来,窗帘鼓了一下又贴回去。李明余光瞥到手机亮起,是周科长发来的:文件下来了,县里要统一外包装,建议站点加套一层,里面不动。李明看了两遍,心里“咯噔”一声——这事,终于来了。
他把手机扣住,等大家看完样箱,回到讲台,像随口提一句:“你们回去可能会碰到一个事——外面要给你们统一一个外衣。我个人的想法是,外衣你们穿,不碍事,但里头别动。外面看上去一样,里面写清楚是谁家的,谁收的,谁装的。出问题,谁站出来。这话我也会跟县里说。”
教室里有人“哦”了一声,有人点头。李明心里那团线头没那么乱了——路不一定非要分了两股拽,只要能用个扣把它们套在一块儿,先过这一阵。
夜里,院里收最后一批货。古丽把一摞写好的小票按顺序排着,苏蔓在旁边念单,声音不快不慢。马合木提抱着一袋枣在门口站了一下,像想说什么又把话咽回去。
“有事?”古丽抬眼。
“没啥。”马合木提嗓子低低的,“就想问一句,以后别老说我家枣‘挑得不够细’了。你看,我这两天学着你说的挑,手都磨起泡。”
“我看见了。”古丽把袋口掀开,果子干净,“过。你看,这样说就对。你挑了,我也看见了。以后我们宣讲,有你一句话,别人听得进。”
马合木提“嗯”了一声,脸上那条紧绷的线松了半寸:“那我先走了,明天还得早起。”
“路上慢点。”古丽叮嘱了一句。
吐尔逊从门外探进头:“冷柜给你们留了半层,别急着塞满。我看今晚风劲儿不小,路上凉,没事。”
“谢谢。”苏蔓冲他摆手。
“谢啥。”吐尔逊把头缩回去,脚步声在门口的石阶上“嗒、嗒”两下,消失在街灯背后。
李明回到宿舍的时候,楼道里已经安静。
他靠在窗边打电话。对面是古丽,声音压得低:“今天有个来借名儿的,谈了一个小时。他的意思是‘你们就写玉尔达,我给你们出包装钱’,我没答应。后来我说,要写就写‘代发’,把来路写明白。他脸拉得老长,说你们这是小气。我说不小气,这是规矩。”
“你说得对。”李明说,“你把锅都甩我身上。谁来问,就说我不在,等我回去一起看。”
“你这人啊。”古丽笑骂,“行,那就都甩你身上。”
“甩我身上,我顶着。”李明笑了笑,转头看窗外那条黑道,“还有个事。县里文件下来了,外面要统一。我想了个法子:外面穿他们的外衣,里面我们不动。你觉得呢?”
“我觉得能行。”古丽想了想,“你把外衣说清楚,别把我们名字遮住。顾客要看,我们给他看里面的字。谁家的,谁负责。”
“就这个理。”
“行,那我明天让苏蔓做一条说明视频。别搞得太复杂,就说清楚‘外衣’和‘里子’,让人一看就懂。”
“好。”李明点头,“你们把院子守住,别慌就好。”
“你也别硬扛。县里那边要是有人说话难听,你就当耳旁风。”
“嗯。”
电话挂断,李明把脑袋靠在窗框上,窗框有一点凉。他把手伸进口袋,摸到那张旧小票——“玉尔达”,纸边被他摩得软了。他心里默念:线别断。
第二天的课,李明没让大家上来讲“经验”,他拉着黑板在教室里走了一圈,把粉笔在四个角轻轻点了四下:“你们各自回去,先把自己那点事干顺。别羡慕别人跑多快,先别跟。你们这会儿就像给院子修路,先把沙子铺匀,把坑填平,别急着压花纹。花纹以后再说。”
他走到窗边,指了指外头的树荫:“你们看,风来了,树影动得不多,因为根扎稳了。”
课后,周科长叫住他:“文件你看了?”
“看了。”李明说,“我打算提个建议——外衣统一,里子不动。外面看着是一家,里面让老乡说了算。出问题,站点站出来,不用都往县里推。这样既能给外面看着好看,也能让里面的人有劲。”
周科长沉吟了一下,点头:“写一份吧,我往上递。”
“好。”
回宿舍的路上,李明把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他知道自己说的是实话,也知道这话不一定那么容易被全盘接受。可他还要说,因为这事儿不是他们这一家站点的事,是他们这条路上所有站点的事。说出来,就像在路边立一根木桩,风再大,也不至于一下把篱笆吹塌。
院子这边,节奏也没慢下来。苏蔓把“外衣”和“里子”的图做成一张简单的图示,左边写“外面统一”,右边写“里面是玉尔达”,中间用一条细线连着,底下压一句:“谁家的,谁负责。”她拍了一条短视频,笑着对镜头说:“我们穿了件外衣,里子还是那个里子。你认里子的字就行。出了事儿,找我们,我们在。”
评论区里,有人问:“那会不会乱?”
“不会。”苏蔓回,“外衣一样是为了好找,里子不一样是为了负责任。”
有人点赞,有人说“明白了”。
晚上,买买提江把车停在吐尔逊店门口,吐尔逊把冷柜门开开又关上,手背在衣服上抹了一下水汽:“温度稳着,路上没问题。”
“走东线再走西线?”买买提江问。
“还是那样。”古丽把小票递过去,“近的后走,让远的先出。你别嫌麻烦。”
“麻烦算什么。”买买提江把小票夹在遮阳板里,“我说过,车稳,人就稳。”
他踩下油门,车子慢慢滑走,尾灯红了一下,又红了一下,最后只剩一点小光点,像远处的一颗星。
周末,县里拉着一车人到了玉尔达。没有彩旗,没有横幅,院里就是平时的样子。有人问负责人在哪儿,古丽说:“去县里了。今天我和苏蔓在,有什么就问。”
“你们就这样干?”一个干部有些惊讶,“也没见你们搞啥仪式。”
“平时也这样。”古丽笑,“你们要看发出去的,就等晚上。要看怎么收,就明早来。要看我们怎么回消息,就座这儿看一会儿。”
“视频谁拍的?”
“我。”苏蔓举了举手机,落落大方,“就找个明亮的地儿,说清楚。老乡听得懂,顾客听得懂,就差不多了。”
这一趟人走后,回去写的感受八成是“风气实”“方法可学”。晚上,这些话摆到了县里几张桌子上。李明没去想谁看了,他只在意这句话能不能换来点实打实的改动。
夜深了,李明又把电脑合上。他把那句“名字不动,外面加”写到了建议里。不是口号,是法子。
他在末尾加了一行字:“人心要稳,路才走得长。”写完,他自己也愣了一下——这话像是从赵书记嘴里出来的。想着想着,他笑了笑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,是古丽发来的:“刚刚有人来问‘你们是不是要改名’,我给他看了里子的字。他点点头,说‘那就行’。这事儿先稳住了。”
李明只回了一个“好”字。这个“好”,不只是“知道了”,还是“放心了”。
隔天,周科长把李明叫到办公室:“你写的东西我看了,行。我往上递,但也得有心理准备——有人会说‘外衣都一样了,里子还要搞这么多名堂干嘛’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李明点头,“到时候我也在场,我来解释。”
“你还要讲课呢。”
“讲课不耽误。”李明笑,“我就讲这事儿。让他们听个真东西,比看十张图强。”
周科长“嗯”了一声,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。杯盖碰到杯沿,发出一声轻响。
傍晚,风有点急。院门口的沙滚了一层,像薄薄的灰色水流。苏蔓按着帽檐,冲屋里喊:“有人来问‘外衣’啥意思,我再发一条短一点的,干脆用比喻——衣服外面是外衣,里面是里子,外面好看,里面贴身。你认里面的字就行。”
“说人话就对。”古丽笑,“你说进去他们就懂。”
她低头给买买提江留条小纸:“今晚走东线再走西线,记得给我回个‘平安到’。还有,吐尔逊那柜子别开太勤,一会儿就到。”
“收到。”买买提江把纸条叠进上衣口袋。
吐尔逊探头:“我把柜门钥匙挂门后钩子上,你们谁用了记得挂回去。别丢。”
“知道啦。”苏蔓冲他摆手,“你瞧你,天天叮嘱。”
“叮嘱才稳当嘛。”吐尔逊笑,“话说出来,人就记得。”
风把院外的柳叶一片片刮下来,落在门槛边。有人用脚尖往旁边一拨,留出一条细细的路。院里的灯温温的,像一只被风吹到半暗里还没灭的小火苗。
县里这边,李明讲完课,背着包往宿舍走。有个学员追上来,是上次坐后排的那个司机:“李老师,我就想问一句,外面统一,里面不动,这话真能成?”
“真。”李明说,“但不是一张纸就能成,是你们回去按这个意思干。你把里子的字写清楚,出了事儿你站出来,外面就没法说你不负责任。你真负责任了,别人也就不再盯着你换不换衣服了。”
司机“哦”了一声,点点头:“我懂了。就是自己把自己站直了。”
“对。”李明笑,“你说得更明白。”
他看着对方离开,转身上楼。走到楼梯拐角,他停了一下,掏出手机给古丽发了条消息:“后天我能请半天假,回镇上看一下。不是检查,就是看看你们。晚上就回来。”
“行。”古丽很快回,“你回来,我给你做一锅炖肉。”
“少放盐。”
“知道你这人嘴刁。”
李明笑着把手机塞回兜里。楼道里有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儿,混着凉凉的夜风。他忽然觉得,县城和玉尔达之间那条路,不再那么远了。不是因为车快,而是因为人心往一处靠。
两天后,李明真回来了半天。院门口那行字还是那行字;白板上的笔迹换了新的一层;桌角的胶带头被人整得服服帖帖。他没说什么,只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,像个远门回来的人,先把院子的气息吸了一口,再走进去。
“人没瘦。”古丽第一句话,“就是黑了一点。”
“你也黑了。”李明回,“晒的。”
“你再说我就不做炖肉了。”
“那我闭嘴。”
屋里热气腾腾,炖肉的香把屋顶都熏得暖暖的。几个人围着桌,谁端谁的碗,谁让谁一筷子。买买提江夹了块肉,咬了一口,冲李明伸了伸大拇指:“你要是天天在就好了。”
“我也想。”李明笑,“可我这会儿还有课。”
“行了,别煽情。”苏蔓打岔,“你回去替我们把话说清楚就行了。”
“我肯定说。”
“你可别说太难。”古丽嘟囔,“说人话。”
“我会。”李明端起碗,往嘴里送了一口汤,咧了咧嘴,“你还是放咸了。”
“滚。”
屋里一阵笑。外头的风在墙角绕一圈,悄悄走远了。灯光把每个人的脸映得暖暖的。李明看着这几张脸,心里那根线被人结了个紧紧的扣,结得踏实。
吃完饭,他把那张小便签塞进文件夹:“明天:外衣照县里,里子照我们。先把话说到位,再把事做到位。”他没给自己留“要不要更多”的问号,只把每一项写得干净。
门外的风略大了些,把门前的叶子吹成一条浅浅的弧。该发的去了路上,该留的进了柜子,白板上的箭头一条接一条,连成了线。
李明站在门口,听见买买提江发动机的声音,平稳,没有多余的响动。他心里说:车稳,人就稳;人稳,路就稳。
回县城的车上,李明靠着窗,手机屏幕亮了又灭,灭了又亮。苏蔓发来一串留言:“有人问‘外衣’懂了没,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比喻图,评论里大多说明白了。有个爱较真的,说‘你们是不是想两头占便宜’,我回‘不占便宜,分清责任’。他没再吱声。”
李明回了个“辛苦”。又补了一句:“你们把院子守住,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。”
“别煽情。”苏蔓回,“等你回来我们再说。”
车窗外天色慢慢深了,地平线一道细细的光像被人用指尖摸过。李明把头靠上去,闭了一会儿眼。他知道,这一段“外衣”和“里子”的事,只是前头一个扣。
后面还有别的扣:县里会不会把外衣改得更紧?外地的合作社会不会绕一个弯子再来借名儿?老乡们会不会因为外衣看起来像一家的,心里生出一丝不踏实?这些都要去接。
但他也知道,一口气不能断。两头的人要在一口气里说话,院子里和教室里要在一口气里呼吸。只要这口气连着,就是谁想拽断,也得多费点劲。
火车远远地响了一声,又沉下去。
风从天山那边往这边吹,穿过枣林,穿过吐尔逊店门口那个结实的冷柜,穿过院子里那口老井,穿过县里教室里的那只样箱,最后轻轻落在李明的掌心里。他把手握了一下,像握住一根看不见的绳。